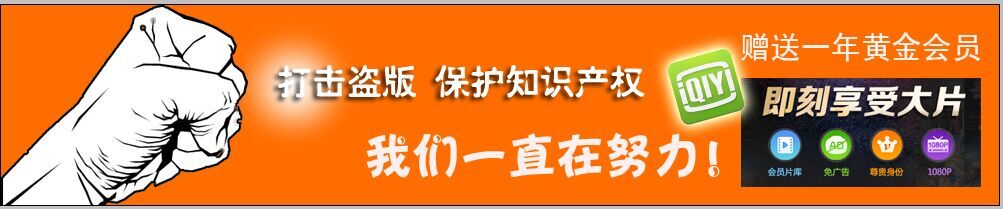“8020萬”����。
這不過是“滴滴打車”(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小桔科技”)四輪融資總額51億元(8.18億美金)的1.6%左右。
如今��,它卻成為“嘀嘀”文字商標持有者之一杭州妙影微電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杭州妙影”)聲討“滴滴打車”商標侵權的索賠金額。
近期���,杭州妙影訴小桔科技商標侵權案件在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杭州中院”)一審開庭。杭州妙影認為����,“滴滴打車”(原名“嘀嘀打車”)應用軟件侵犯了自己的商標權�����,要求對方賠償8000萬以及20萬律師費等,同時在媒體發表聲明�����,消除影響���。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滴滴打車”第一次因涉嫌商標侵權被訴至法院。2015年4月1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海淀法院”)正式審結廣州市睿馳計算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州睿馳”)訴小桔科技侵犯商標權一案。
短短一月時間����,小桔科技兩次出入法院��,案由均系涉嫌侵犯他人商標權�����,這足以說明小桔科技在“滴滴打車”商標保護上的“硬傷”,但是�,8000萬商標索賠額是否系“嘩眾取寵”之舉?杭州妙影案勝算又有幾何?
“8000萬”索賠額:是否系“嘩眾取寵”的一場鬧劇?
“為什么是8000萬”?杭州妙影的理由是���,滴滴打車是小桔科技唯一的產品�����,公司所有的獲利都依賴它。8000萬就是從侵權獲利中計算出來的����。
杭州妙影羅列了3種計算方法:
第一是資本市場的獲利�����。2014年小桔科技獲得了1.8億美金的融資,并從騰訊那里拿到了超過14億的打車補貼,另外還有合作廣告商的補貼。這么一算小桔總共有20億的獲利,5%就是1個億���,所以主張8000萬不過分。
第二是軟件下載量�。截至2014年3月�����,小桔科技的嘀嘀用戶達到1個億����,也就是說侵權的商品達到了1億件,按每件侵權商品賠1塊錢算,也遠遠超過了8000萬�。
第三是遭受的實際損失�����。小桔科技的滴滴打車已經覆蓋了全國178個城市,導致了杭州妙影自身商標和產品嚴重割裂,這都是因為滴滴打車投入了天價營銷費用實現的����,妙影要打開產品知名度�����,就要增加相當多的廣告投入,從騰訊為小桔科技注入的14億來看�,8000萬也是很少一部分���。
那么�����,如果小桔科技真的被認定構成侵犯杭州妙影的“嘀嘀”文字商標專用權,到底應該賠償多少呢?
根據商標法第六十三條規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除去為制止侵權的合理支出外,確定方法有三種:其一,“實際損失”�����,即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其二��,“侵權所得”��,即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其三�����,“商標許可費用”����,即參照該商標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
此外�����,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
值得一提的是的�����,這三種賠償數額的確定方法是有先后順序之分的。如果不能確定“實際損失”,就按“侵權所得”計算���,如果“實際損失”、“侵權所得”都不能確定,則按照“商標許可費用”確定���。
而針對“實際損失”�����、“侵權所得”等具體的認定方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十四條規定,侵權所獲得的利益�,“可以根據侵權商品銷售量與該商品單位利潤乘積計算;該商品單位利潤無法查明的����,按照注冊商標商品的單位利潤計算���。”
《商標案件司法解釋》第十五條規定����,實際損失“可以根據權利人因侵權所造成商品銷售減少量或者侵權商品銷售量與該注冊商標商品的單位利潤乘積計算。”
顯然���,根據上述兩種計算方式,即使滴滴打車真的侵犯杭州妙影的商標權�,杭州妙影也很難舉證證明自己的實際損失���,而滴滴打車因為服務免費���,也很難證明其所得利潤���,不過�,滴滴打車曾與很多廠商合作“打車補貼”�,品牌合作部分的收入應可計為收入。
根據商標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當無法確認“商標許可費用”�、“實際損失”或“侵權所得”時��,法院可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三百萬元以下的賠償���。
那么���,小桔科技在被訴之前的融資額能與侵權所得劃等號嗎?顯然不能如此認定����。一般公司獲得的融資額都有約定用途�,或用于擴大經營或用于研發投入,其本質是擴大了注冊資本額,分散了公司股權�����,應該算是股東層面的交易,但此種投資或入股行為與公司直接經營所得���、銷售利潤等并非一個概念。
因此��,杭州妙影主張的“8000萬”商標侵權索賠金額及其計算方式�,可能缺乏明確的法律支持,即使法院真的認定滴滴打車侵犯其商標權�����,最終判處的賠償額也會遠遠小于此數字����。
那么,小桔科技的“滴滴打車”會否被認定構成侵犯了杭州妙影的“嘀嘀”商標專用權呢?
“滴滴”是否侵權:前案認定判決邏輯會否被本案采用
誠如本文開頭所言��,4月1日����,海淀法院剛審結一起廣州睿馳訴小桔科技侵犯商標權一案��。該案判決有兩點至關重要�����。
首先,該案判決認定“滴滴打車”不屬于“電信服務類”����。海淀法院判決認為����,第38類服務類別為電信�,主要包括至少能使二人之間通過感覺方式進行通訊的服務,設定范圍和內容主要為直接向用戶提供與電信相關的技術支持類服務。該類別中所稱提供電信服務需要建立大量基礎設施,并取得行業許可證。“滴滴打車”平臺需要對信息進行處理后發送給目標人群,并為對接雙方提供對方的電話號碼便于相互聯絡。上述行為與該商標類別中所稱“電信服務”明顯不同,并不直接提供源于電信技術支持類服務����。
其次�����,該案判決認定“滴滴打車”不屬于“商業服務類”。 海淀法院判決認為,第35類商標分類為商業經營����、商業管理���、辦公事務�,服務目的在于對商業企業的經營或管理提供幫助����,對工商企業的業務活動或商業職能的管理提供幫助�����,服務對象通常為商業企業�����,服務內容通常包括商業管理、營銷方面的咨詢�、信息提供等��。
“滴滴打車”提供服務過程中的相關商業行為,或為小桔科技針對行業特點采用的經營手段��,或為該公司對自身經營采取的正常管理方式�����,與該類商標針對的由服務企業對商業企業提供經營管理的幫助等內容并非同類��。
海淀法院判決認為,廣州睿馳所稱其商標涵蓋的電信和商務兩類商標特點���,均非小桔科技服務的主要特征,而是運行方式以及商業性質的共性����。�����、
鑒于“滴滴打車”服務與廣州睿馳注冊商標核定使用的類別不同�����,商標本身亦存在明顯區別����,其使用行為并不構成對廣州睿馳的經營行為產生混淆來源的影響,法院認為小桔公司對“滴滴打車”圖文標識的使用�,未侵犯廣州睿馳三項注冊商標專用權�����,該公司的訴訟請求不能成立。
那么��,在杭州妙影訴小桔科技的“嘀嘀”文字商標案中�����,小桔科技是否能再次“幸免于難”呢?
商標局網站(中國商標網)查詢結果顯示�,杭州妙影持有的9類“嘀嘀”文字商標于2011年3月22日申請�,2012年5月21日被商標局核準注冊,核準使用的商品或服務類別包括:計算機程序(可下載軟件)�����、信號燈�、手提電話、探測器�����、電線��、傳感器����、遙控儀器���、電子芯片����、電池充電器等��。
從時間上看����,杭州妙影所持有的“嘀嘀”文字商標核準注冊時間遠遠早于小桔科技的成立時間��。
從使用上看���,在案證據顯示���,2011年8月開始�,杭州妙影就推出了“嘀嘀出行”的下載軟件����,后來還有“嘀嘀導航”、“嘀嘀地圖”、“嘀嘀打車”��,主要在杭州地區推廣���,直到現在也還在持續使用中�。
顯然,杭州妙影的對“嘀嘀”文字商標的使用領域和場合與小桔科技改名前“嘀嘀打車”基本類似或相同。
在杭州地區,在小桔科技發展壯大前,存在兩個“嘀嘀打車”足以讓當地消費者發生誤認或混淆����。
那么�,小桔科技此前使用“嘀嘀打車”是否構成侵犯杭州妙影的“嘀嘀”文字商標專用權呢?
根據杭州妙影所持有的“嘀嘀”文字商標核準使用的商品或服務類別來看,小桔科技的“滴滴打車”運營過程中,需要用戶下載及安裝客戶端軟件(APP),似乎會落入杭州妙影所持有商標的核準類別之內——計算機程序(可下載)。
但是�����,誠如此前海淀法院就廣州睿馳訴小桔科技做出的判決����,最終杭州中院是否會認定小桔科技構成商標侵權�,是否需要承擔賠償責任,則完全取決于法院是否會認定小桔科技的“滴滴打車”APP下載、安裝及使用,屬于“計算機程序(可下載)”服務��。
如果杭州中院完全采用海淀法院的判決邏輯��,認定小桔科技的“滴滴打車”雖然服務過程中需要用戶下載安裝APP程序��,但是,“滴滴打車”提供的服務本質是“打車”等交通信息服務,而非程序下載服務。那么,小桔科技將可能“再逃一劫”。
屆時“8000萬”商標侵權索賠額則可能會淪為一場“鬧劇”���。